每期目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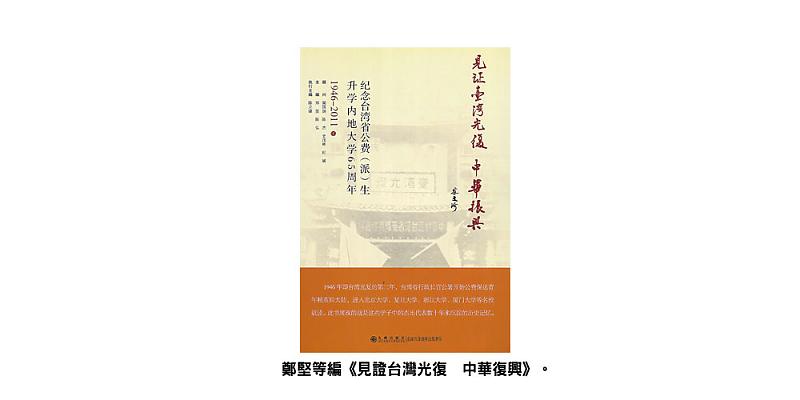
1946年,台灣光復的次年,近百名優秀的台灣青年通過公費考試,前往大陸八所大學讀書,且看他們怎麼看日本殖民統治台灣,以及台灣光復時的心情。
70年前,台灣光復第二年(1946),台灣省政府招考一批青年,公費保送到大陸升大學。四、五百人應考,近百名被錄取,保送到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浙江大學、廈門大學等八所高等院校。其中有從日本留學歸來的,有在台北帝大肄業的。2011年我及另一位老公費生陳弘整理出版了這批台籍青年的回憶錄(《見證台灣光復 中華復興》,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次年出版了繁體字,書名改為《欣見台灣光復 又逢中華復興》)。本文以下摘錄書裡的部分內容,讓更多人瞭解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歷史真相。
嘗盡被日本統治的滋味
洪瑤楹:1945年5月,在台中讀書的我因為下中國象棋,被日本教師痛打,受到訓誡處分。同年6月,又因為沒有給日本員警敬禮,被連打帶踢捆綁拘留。此類對台灣人的歧視屢見不鮮,使我深深感受到作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屈辱。「我是中國人」的強烈民族感刻印在心中,從此便盼望台灣光復回到祖國懷抱。
廖天朗:在台中一中讀書時,我利用柔道的優勢,幾次和同學們一起,在夜色朦朧下痛打那些白天欺壓我們的日本學生,以泄民族之恨。在每週例會上,校方侮辱我們是「清國奴」,欺壓台籍學生時,我們台籍同學一起發出鼻音「嗚」,以示抗議。校方上前制止,「嗚」聲此起彼伏,連續不斷,迫使校方無法應對。
楊玉輝:我至今還記得1942年秋天在學校發生的一件事。下午最後一節課臨近下課時,日本老師忽然談起一種糖,說這種糖本來是紅色的,含在嘴裡就變成綠色,再變成黃色……說到這裡他話鋒一轉,「這就是支那人,支那人就是變來變去,毫無誠信的變色龍!」剎那間,他的話被全班同學的噓聲所淹沒。他氣急敗壞,鐵青著臉,聲嘶力竭地喊叫:「是誰!有種的站起來!」沒有人說話,沒有人站起來,全班鴉雀無聲。老師一籌莫展,留下一句「沒有人承認不下課」,悻悻地走了。一小時、兩小時,天暗了,到晚上7點還是沒有人承認,老師只好讓同學們回家。
陳澤灸:日本殖民者在戶籍管理中分內地人(日本人)和本島人;戰時配給的糧、油等生活用品額度也各不相同;教育系統也是為了配合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政策,不但教師用日語授課,課本內容盡是「皇民化」教育,台灣學生的升學也受到限制,多數學生報考理工科的學院,報考文科類別沒有出路,因為殖民當局怕台灣學生將來從事政治活動,反對殖民統治。
曾重郎:我讀一年級時,同班的日本學生重久常跑到我課桌前騷擾,不讓我看書。有一次,我實在忍不下去了,站起來把重久推到教室後頭,並將他按倒在地上,但沒有動手打他。重久的父親是警長,重久託比我高年級的員警兒子管野來教訓我,管野一猛拳打在我鼻樑上,我頓時鼻血直流。
謝發楸:我出生在苗栗縣客家人居住的鄉村。在殖民統治下,台灣人被迫接受各種各樣的「差別對待」。當時管轄新竹、桃園和苗栗三個縣的新竹州內只有一所新竹中學,該校招收150名學生,優先招收日本人,而且台灣人不得超過半數。
武裝起義要光復台灣
方舵:我1926年生於台北市,原名黃厚年。父親黃石養是個煤礦高級職員……直到1937年秋,才知道父親不顧個人安危,不顧三個孩子尚小需撫養,他和礦主及工人們毅然組織抗日團體,秘密製造刀、鏢等武器,組織武裝起義,要光復台灣。父親還親赴新加坡、印尼等地聯繫,發動華人共同抗日。日本1940年5月在全台下了拘捕令,數百人被捕,殘暴拷訊屠殺,台灣礦工72人慘死。父親就是罹難者之一。母親悲憤交加,突發腦溢血而亡。尚未成年的哥哥靠半工半讀養活我和弟弟,並供我們上學。
黃瑞霖:我父親黃朝生追隨蔣渭水參加抗日活動,先後參加文化協會和民眾黨。因為沒有按照殖民當局的「皇民化政策」改成日本姓名,我們遭一些日本人歧視和侮辱,被罵為「清國奴」。又由於在台北市同年級學生武道單打比賽中得了冠軍,我被外校的日本學生圍打得鼻青眼腫、頭破血流。
陳伯熙:我們在基隆中學畢業前夕,自發地舉行惜別晚餐會,互相傾吐五年來受欺淩的痛苦,最後決定做一個刻有F字頭、表示台灣人的皮帶扣,並在畢業紀念冊上相互鼓勵,有的寫「血濃於水」,有的寫「以血換血」等等,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。後來紀念冊被日本同學發現,告到校方。校方認為這是一次反日活動,還懷疑台灣同學秘密結社,立即上報基隆員警署,結果五名同學被扣留審訊,其餘被員警抄家和給予無限期停學的處分。這就是基隆中學F-mix(台灣人)事件。
我們的根在大海那一邊
蔡海金:1927年我出生在苗栗縣一個農村家庭。日本強行「皇民化」運動,要我們改姓名,但父親經常告訴我們,「我們來自福建泉州府同安縣,我們是中國人,我們的根在大海的那一邊」。
羅美行:年幼時在家裡講客家話,小學一年級開始學日語,三年級以後全部講日語,違者要受到嚴厲的懲罰。14歲那年我考進台北工業學校,老師都是日本人,學生九成以上是日本人,為數很少的台灣學生經常受欺負。隨著年齡增長,我漸漸感受到亡國的痛苦,心中的民族意識日漸增強,心底萌發出一個念頭:做事一定要比日本人強。
鄭鴻池(又名鄭堅):我們鄭家跟隨鄭成功從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鎮入台開拓,已在台繁衍十多代。我們都是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的歷史見證人。
楊威理:大連三中實施的是徹底的效忠天皇教育,但父親經常告訴我:「絕對不可忘記自己是中國人!現在是沒有辦法了,只好忍痛蟄伏一個時期。」有一件事情我終生難忘,那就是父親曾在他的手掌上寫一個大大的「漢」!
張克輝:日本投降後,沒有老師教國語,學生就自己買《自學國語》小冊子,互相高聲朗讀,「你好嗎?好久不見了。」「謝謝,我很好。」「我是中國人,你是中國人嗎?」「我是中國人。」
1947年夏天,彰化市教育局在彰化公園的戲院,組織一場演講會。上台演講的是幾位正在大陸念大學的台灣公費生,有杜長庚、江濃、許夢雄(徐盟山)、鄭鴻池(後改名鄭堅)等。從他們的演講中,我知道大陸青年正在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鬥爭,意識到新時代的青年應該負起改造社會的職責。會後,我們幾個青年同學還到孔子廟討論人生的理想和前途。從那時起,我心裡萌發了回大陸求學的念頭。
方木:1946年2月,我們在日本的一千多名台胞乘坐「高砂丸」客輪回到故鄉台灣。同年6月我報考北京大學被錄取了。不久,台灣各院校也開始招生,又報考了台北師範學院英語專業,也被錄取了。面對兩張錄取通知書,經過一番思想鬥爭,最後選擇回祖國大陸學習。
楊玉輝:1946年12月初到上海暨南大學報到。14位公費生都積極參加學生運動,有的被開除,有的不得不離開學校。杜長庚、許夢雄(徐萌山)、羅美行(白明)到了解放區,張璧坤回台參加台灣「四六」事件,後被槍決。劉碧堂回台,被捕入獄在獄裡病死。丁保安回台被捕,後出逃到日本。劉榮超回台念台大,畢業後赴美,留校任教。盧國松、李天贈上海解放前夕先後被捕,上海解放時獲救。1949年6月我和盧國松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。
(作者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