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期目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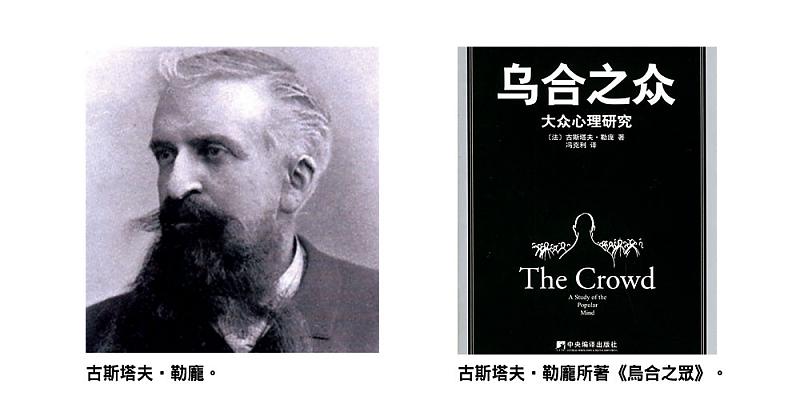
勒龐(Gustave Le Bon)生於1841-1931年,是一個法國人,而「太陽花」則是2014年3-4月發生在台灣的事件,兩者風馬牛不相及,為什麼會把它們放在一起呢?
因為台灣有人讚揚「太陽花」是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、高度民主成熟的運動;有人讚揚它體現了台灣「高素質的公民社會」,「50萬人上街,秩序井然,主持人一宣布散場,半小時內現場清空,連一包垃圾都沒留下」。大陸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多元參與、動員效率高的「新社會運動」。我的看法則不同,因為「太陽花」讓我感到「似曾相識」,於是想起了《烏合之眾》這本書,想起了其作者勒龐。是他,早在1895年,似乎就已經描繪了「太陽花」的輪廓與圖像。
從眾心理
所謂「從眾心理」,就是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行為。勒龐稱之為「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」,個體情願把群體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。這就造成了一些重要後果,如教條主義、偏執、人多勢眾不可戰勝的感覺,以及責任意識的放棄。「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;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、想法和信念,他們或者全盤接受,或者一概拒絕,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。」
「太陽花」是從眾心理的充分體現。許多參加者並不知道什麼是「服貿」,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反服貿。有的是「本身無所謂,旁邊人去了於是大家都一起去」;「絕大多數都回答,我不知道服貿是什麼東東、但大家要反,我就跟著反」;「近兩年反馬、反國民黨、反中是潮流,不反一下就不潮了」;從台南北上的學生說:「反正放假、有車有吃有喝,就來台北逛逛」;甚至有人說:「不用上課了,去立法院鬥地主通宵打波去?走啊弟兄們」。據調查,一般民眾,有80.9%表示對服貿協議不了解或一知半解,許多學生是通過歪曲事實的「懶人包」來了解服貿的。
在從眾心理的影響下,正如勒龐所說:「有意識人格的消失,無意識人格的得勢,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。」「太陽花」的參與者說:「如果不去現場打卡(報到),會覺得跟不上流行,在朋友間很沒面子」;「我反黑箱服貿,可是未必反服貿。然而這樣的言論,在目前學校同儕間,已經不僅是一個不同意見,而是一個奇人異說,只要在網路上和主流意見稍有不同,大量無情的訕笑和貼標籤就隨之而來」;「凡是有反反服貿、不支持學運的言論都會K得滿頭包」。因此,參與者認識到,反服貿真理,已經使得自己懂得閉上嘴吧,形成寒蟬效應。這說明在「太陽花」之下,人們只能把「反服貿」當作「絕對真理」而全盤接受,其他想法只能是「絕對謬誤」,給予一概拒絕。「太陽花」的言行證實了勒龐的一個觀點:「個人可以接受矛盾,進行討論,群體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」。
群體的道德
勒龐對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有如下的描述:衝動、易變、急躁;易受暗示和輕信;情緒的誇張與單純;偏執、專橫和保守;放棄責任意識,「不會受到懲罰」等等。
媒體報導了「太陽花」的「急躁」和「衝動」:「是因為張慶忠的作法引起全民共怒,而由他們登高一呼,開始抗爭」。「得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在30秒內趁亂將服貿送出委員會,所有人都氣炸了。當晚,一群朋友相聚,即著手討論進一步的行動」。
「拆卸門板、打破玻璃、掀翻桌椅、扯下窗簾、破壞天花板且又行竊」;「大門口的防護鐵絲網被用老虎鉗剪斷、玻璃被砸碎、房門被拆、辦公室內文件亂丟、天花板掉落」;「拆除立法院匾額,撞傷警衛,破壞主席台、議場的辦公桌椅,侵入私人抽屜領域,牆上塗鴉等破壞行為,嗣再倒掛國旗,場內喝酒慶祝,玩親親、自拍等遊戲,已逾越法律非暴力的範圍」。
此外,「封鎖立法院四周出入口與街道,公然盤查車輛,不准任何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官員離開」;「自認有權任意占路癱瘓交通,圍人限制自由」;「幾百暴民把忠孝東路、林森南路口堵住,幾十路公車被迫開門下客,十餘萬用路人被迫改道,或在暴民的狂吼及辱罵中冒險通過」;「暴民圍堵立法院,趴上立委座車的引擎蓋、跳上車頂、踹凹車門、砸破車窗。綠委蕭美琴在圍困中被嚇得花容失色,大罵:這就是我們要的民主嗎?」
「太陽花」也表現出易變的特點:它的訴求有如下變化:「第一天沖進立法院議場之後,學生們所拉起的布條是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;接著轉為要求退回服貿,捍衛民主;再來轉為先立法,再審查,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學者提出的《兩岸協議締結條例草案》通過立法作為運動首要的目標。3.23學生攻占行政院之後,運動的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。到了3.30在凱達格蘭大道的集結,林飛帆與陳為廷英雄式的出場(夾道民眾歡呼選總統)」。
「太陽花」還表現出輕信。服貿「開放什麼都搞不清楚,就跟著大家一起高喊中國要買下台灣」。很多參與者輕信「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」、「開放大陸勞工來台就業衝擊台灣百萬勞工」等五大謠言。媒體報導「在現場問一名學生,為什麼要反服貿?才18歲的她回說,服貿通過會有很多大陸人來搶飯碗。追問她,搶哪個行業的飯碗?她說不知道。再問她,學生占據立法院,讓政府議事停擺,對嗎?她說是政府不對在先。政府哪裡不對?她就只會搖頭不再答話」。這正如勒龐所說的:「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」;「一個人編造的奇蹟,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」。
「太陽花」還表現出偏執、專橫、保守:「在街頭,他們任意霸占道路,從不覺得有需要依法申請;他們隨意攻擊官署,還宣稱只是路過;他們恣意羞辱人民選出的立委,干擾他們人身與行動自由!在網路上,只准許一種聲音存在,只要出現不同意見者,立即群聚圍剿,甚至進行人肉搜索、癱瘓特定網站,只求消除不同的聲音!相對照他們所一再倡言的審議式民主,真的是絕大諷刺」。「這場運動還充斥著濃濃的排他主義。只要反服貿就是愛台;只要支持服貿或不反服貿,就是賣台。尤有甚者,一股無人譴責的排外種族主義氛圍無聲瀰散」。「對於某些意見不同的評論者,不僅進行言辭圍剿,還口出髒話。只要在網路上和主流意見稍有不同,大量無情的訕笑和貼標籤就隨之而來」。「身為10A總裁的彭淮南先生認為簽服貿是好的,消息一出,曾任金管會或經建會高層的人士馬上跳出來,直言彭總裁說錯了。為何他們如此確定別人是錯的,而自己一定就是對的?」。學生們還專橫地提出:「馬、江道歉下台」、「服貿重啟談判」、「停止兩岸協議」等,顯示出「高傲,毫無妥協餘地」。這和勒龐所說的,如果有人做出最輕微的反駁,「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地叫駡」、「專橫和偏執是一切類型的群體共性」十分相似。
那麼,他們為什麼敢於做出這樣違法的行動呢?勒龐指出:「孤立的個人很清楚,在孤身一人時,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,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,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。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,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,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,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」。「孤立的個人在生活中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,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群體時,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,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」。「太陽花」的參與者似乎都有一種共識:「群體為國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」。不僅是他們,台灣還有不少人支持他們,似乎「人多勢眾」不可戰勝,大家都可以「放棄責任意識」。
領袖人物
勒龐對群體的領袖人物也有所描述,這裡只舉幾個事例:
他說:群體的領袖「具有支配群體大腦的能力」,他們能夠讓群眾相信,「他們看到了自己並沒有看到的事情」。又說:「群眾在服從他們時,要比服從政府溫馴得多」。
「太陽花」的領袖們可以讓群眾相信他們看到了服貿的「黑箱」,相信他們提到的「反黑箱」完全是正確的;讓群眾相信他們提出「退回服貿」等主張都是正確的。讓群眾相信他們能夠「代表台灣人民」,可以成為「這個國家的總指揮」。他們聲稱運動中的一切所做所為(當然包括違法行為),都是依循所謂「公民不服從」的法理,相信他們是在挽救憲政和民主,不但不應當受到懲罰,還應該被當作英雄受到歌頌。
勒龐所說的群體領袖「說服的手法」,似乎在「太陽花」得到完全的證實。他指出,群體領袖影響民眾的三種手段是:斷言法、重複法和傳染法。「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,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」,「一個斷言越是簡單,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,它就越有威力」。
「太陽花」提出「斷言」,諸如「反服貿」、「反黑箱」、「退回服貿」、「守護台灣」、「公民站出來」、「馬江道歉下台」、「服貿重啟談判」、「停止兩岸協議」、「民主與專制的對決」、「愛台灣」、「台灣魂」、「反馬」、「反中」等等,而且一再重複,讓它傳染到廣大民眾之中,這樣,它就成為「台灣人民的聲音」了。
社會運動需要吸取教訓
好了,有關勒龐與「太陽花」的類比,就寫到這裡吧。從以上類比,可以看出「太陽花」與勒龐100多年前的描述確有一些「驚人的相似之處」。當然時代不同了,二者不可能完全相同。如果有人願意把「太陽花」與勒龐的描述不同之處進行比較,說明「太陽花」的進步,那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。
勒龐的《烏合之眾》並不完美,它的意義在於「發現問題的功能,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」。把它與「太陽花」相比,也只能發現一些問題,並不能為解決這些問題開出藥方。
應當指出,我寫這篇文章絕對不是有意貶低「太陽花」、貶低台灣的社會運動(或稱公民運動),而是找到了一面鏡子,可以照出「太陽花」並不完美的一面,讓大家看到它的不足。我認為台灣的社會運動,從紅衫軍、白衫軍直至這次黑衫軍,一路走來,需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,即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,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,還存在不少問題,而民粹主義的色彩可能是它的「硬傷」。
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人們,應當從中總結經驗教訓,才能讓它一路走好。千萬不要聽信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,把它吹捧為「台灣高度民主成熟的運動」、「高素質的公民社會」,那是把大家美好的理想低俗化了,那是對公民運動的褻瀆,那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「捧殺」。
(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