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期目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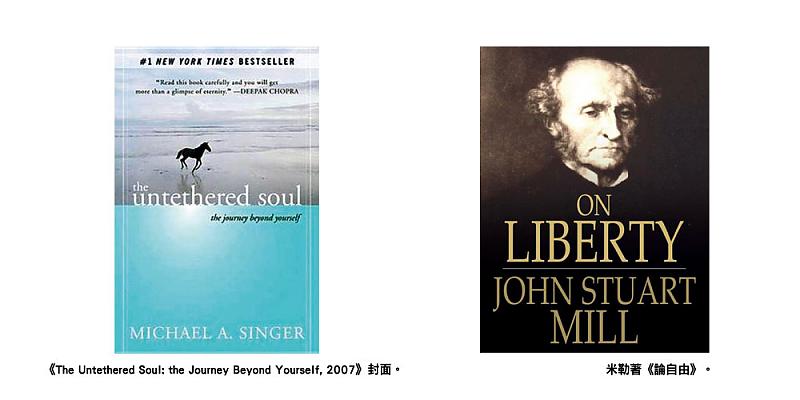
有水不知無水之苦,無水苦境對水卻有著過度的渴望。這是當代社會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經歷長期演進之後的寫照:經歷幾千年集體主義的中國,引進西方市場經濟之後,對個人自由主義有著過高的憧憬;於此同時,承繼並發揚傳統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國,在運行200多年後的金融資本主義下,逐漸產生了「異化」現象,對著集體主義的治理也有著深厚的迷思。
最近,曾經來台研習的大陸研究生,透過電子郵件,要我釐清公民意識概念及其間的關係。針對此請求,我簡單解說如下。
所謂「公民意識」,乃近代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的產物。因為現象的主體是意識,顯然是立基於個人的認知。認知什麼呢?認知個人在外在生存網絡中的身分定位;Michael A. Singer在《不受限制的靈魂》(The Untethered Soul: the Journey Beyond Yourself, 2007)書中指出:意識其實是感受你腦中的「事實模型」,而非事實本身。外在的網絡又是什麼特性呢? 以公民意識而言,就是公民網絡。
首先,我們應瞭解:民與人是不同的。民者,根據孫文的解說,是有團體、有組織的眾人,換句話說,就是「具有群性的個人」;缺乏群性的個人不是民。儘管如此,在個人自由主義的體系中,到底個人是否具有群性屬於心理狀態,很難驗證和規範,再加上,個人自由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中被認定是天賦的權利,不受侵害。但是,米勒(Stewart Mill)在《論自由》(On Liberty)一書中又明確定義,個人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。因此,群性的規範只能限定在公共領域,也就是說,民的群性只能限定為公民身分,不能擴大至個人的私領域,個人隱私權應受保障。
然而,心性很難以法律或體制加以規範,只能規範心性所表現出來的行為。所以,公民意識就超越了公民社會或公民體制的範疇;但是,沒有公民意識,就不會有合理運行的公民社會或公民體制。關於公民意識,葛蘭西(Antonio Gramsci)認為它是公民個人與社會之間自我調解的理性,亦即公民社會維護個人自由的潛力。當代公民社會,一方面基於個人化精神,獨立於國家之外運作,另一方面,又要形成集體認同和集體意識,這種二元統合的社會機能就是公民意識。因為弔詭,所以體制的建構相當不易,非一蹴可及。
由此可以進一步瞭解,公民意識或公民社會的形成,必須經歷長時間的公民教育及公民體制的實踐經驗,才有可能。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或傳統威權體制國家,在推動民主化時,常常都陷入混亂而失敗的原因。台灣及菲律賓的民主化就是失敗的明顯例子。
相對來說,這與東方集體主義的概念是有其差異的;集體主義的主體是社會群體,而個人是附屬於群體當中,群體意識是主軸,但群體意識並非上天所賦予的天性,它的形成,是因為有個體的存在,所以群體意識必須重視個人的生存與發展;這就是中國民本思想中「民貴君輕,社稷次之」的真諦。換言之,集體主義就是重視個人生存與發展的群體、允許個人身分設定的群體。然而,可讓個人有身分定位的集體,顯然又需要有強制性的群體秩序和規範。
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,由於自然界對生存的威脅促成了個人的群性需求,這種人與自然的鬥爭形塑了以權力為本質的秩序。自然而然地,集體秩序就會以權力來規範,這就是孫文在「民權主義」所說的「神權和君權」。西方從君權轉型到民權是經歷過「思想層次的反省和批判」;從根本改變其生存意義,重新做群性與人性的身分定位,進而才能採取向君權體系奪權的革命行動。顯然,思維決定行為,沒有革命性的思想變革,就不會有革命性的行動及革命性的體制變革。曾有人說,傳統集體主義的社會不適合實行個人自由主義的民主體制,聽起來甚為刺耳。終究,制度的演進無法擺脫時間、空間對人的長期影響;思想的變革很難一蹴可及,制度又是思想的產物,因而制度轉移不但不易,且有相當程度的風險。
但是,另一方面來看,再好的體制,一旦運行產生異化,也將崩壞,這也是這一世紀以來,資本主義造成西方民主體制快速異化,令許多西方有識之士擔心,甚至恐慌,反而積極探尋東方集體主義價值的「可引用性」。事實上,個人自由主義社會及集體主義社會都是政治學大師韋伯(Max Weber)所定義的「理想類型」(ideal type),就是社會體系光譜的兩個極端,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存在的。現實的社會都是「個人與群性的共生和融合」,也就是個人意識中存有群性;群性的體制中融入人性。
任何社會一旦逐漸邁入兩個極端,都會產生異化,都不是人類之福。這也就是日本SONY公司前總裁出井伸之所說的:社會主義美國及資本主義中國,這兩種型態都是原來體制的異化之後,試圖尋求共生或融合之策,成功與否,只能拭目以待。這種趨勢又印證了中國道家所說的「物極必反」;共生與融合或許將成為未來體制生存與發展之道。
(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