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期目錄

1988年6月第四次會面
又過了兩年,1988年的5月22日,自美東飛抵香港,24日轉往廣州,出席在中山大學召開的陳寅恪學術研討會,會後於6月2日清晨飛抵北京,宿於玉淵潭之望海樓,步行可至錢府,遂於6月2日下午3時往訪。錢先生垂詢廣州陳會經過後,謂陳先生不喜共產黨,瞧不起國民黨,既有遺少味,又不喜清政府,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,並重申前說。
我問馮依北究系何人?答稱據知馮原姓劉,詩中如徹骨云云,宋詩多見。我曾寄先師蕭公權《跡園詩稿》與《畫夢詞》,故問意見,錢先生答稱蕭先生自是名家,今能此者已不多,惟不免舉輕若重耳。葉公超亦喜作舊詩,差蕭先生遠矣!因謂許多名人之透明度,日見昭然,如毛、如魯迅皆然。歷史確須不斷重寫,即因透明度之日見昭然也。
我曾寄胡頌平記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》,其中胡說未曾見過錢鍾書,錢先生曾回函說博士健忘。此次又提到此事,錢先生說不僅見過,而且見過三次。第一次在上海合眾圖書館。第二次在陳衡哲家吃飯,陳以蟹殼黃小燒餅待客,胡嫌寒酸,故印象深刻。第三次談時事,大意具見胡日後發表之Stalin'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中。錢先生曾提到胡適品格高,因當時世人皆以為胡不二色,尚不知胡身後出現不少豔聞也。
錢先生謂近年收到不少台灣出版之書,少見精彩之作。錢賓四雖是史家,然其回憶錄極不可靠,所記事之時間也多舛誤,若謂在常熟見到子泉、鍾書父子,大謬不然,錢先生說生平不曾到過常熟,感歎如此歷史與「fiction」何異?今日回首往事,侍談極歡,甚感與錢先生相識恨遲,相見恨不永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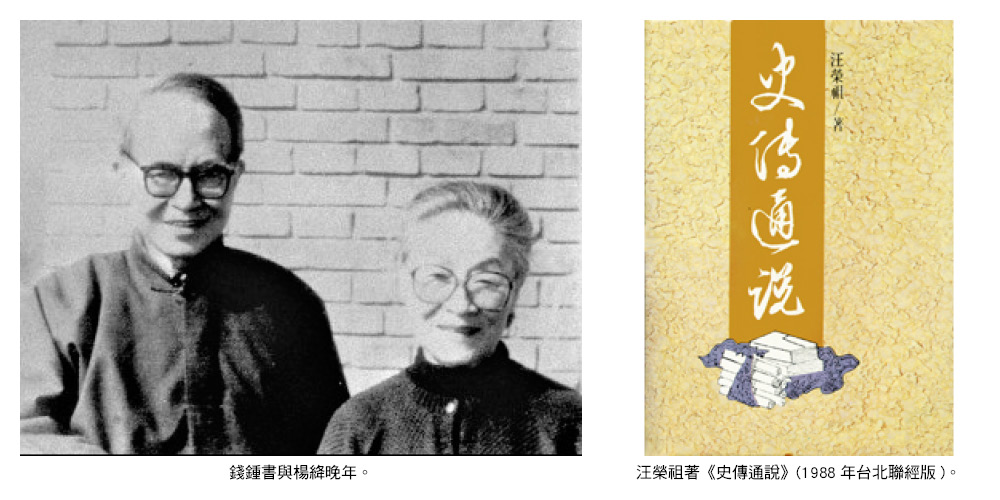
1989年後被病折磨
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,震動一時,我曾去信問安,7月13日楊先生回函說:「北京動亂,謠言滿天飛,官話當然不如謠言動聽,但我等身居此間,深知官話非全飾說。我等皆安好,請勿念。」錢先生附筆說:「奉書彌感關注,愚夫婦托庇平善,此生尚有晤面期也。17世紀英國詩人Earl of Roscommon有言:『It was best to sit near the chimney when the chamber smokes』,言殊中肯,吾兄尋味之,一笑」。後來收入《槐聚詩存》的《閱世》七律,即記此感也。
錢先生於1989年之冬,劇發喉炎,牽動哮喘宿疾,來信說:「幸醫藥及時,未致狼狽,然奄硠二月餘,亦甚委頓」。1990年後,右拇指痙攣,「舉毛筆如扛鼎,用鉛筆寫亦不能成字,甚矣吾衰」!此後錢先生病軀日衰,常住醫署,未便造訪,但從通訊中,可知他病得很辛苦。他於1994年2月23日來函有云:「去春住醫院三月,臥手術臺上六小時,割去左腎(乃Big C),內人陪住醫院,辛勞萬狀,渠身本患血壓、心臟,以此加劇。出院後又逢寓所修繕,椓椓丁丁,晝夜喧擾,如是者又四月餘。現在愚夫婦皆惶惶以就醫服藥為常課,謝絕一切外務。」此為1993年3月5日動的大手術風險很大,幸而順利完成。
1994年7月,錢先生因肺炎住院,卻又發現膀胱中有癌細胞,經由鐳射切除很成功,但導致僅存的一腎,功能衰竭,利用人工腎應急,一個多月後始解除危機,改用「透析」(haemodialysis)法,使腎臟功能有所恢復,在扶持下可走幾步路。到10月底又因感冒而引發高燒,變得極為虛弱。因用藥無效,高燒不退,精神不濟。錢先生病情反覆,甚是辛苦。
到1996年,錢瑗也病倒了,入住西山腳下的北京胸科醫院,我與內人曾寄卡祝她早日康復,並寄送《理智與情感》英文版錄影帶,讓她在病中觀賞解悶,她很高興,對病情表示樂觀,哪知檢查的結果是肺癌晚期,自此再也沒有接到她的來信。他們仨感情深厚,錢瑗得了重病瞞著母親楊絳,楊絳知道後,更不敢告訴臥床多年的錢先生,最後還是瞞不住,也免不了刻骨銘心的悲痛。錢瑗於1997年3月4日病歿,錢先生於翌年12月19日逝世,只剩下楊絳一人年過期頤。
錢先生謝世後,楊先生曾於1999年初惠函,我於1月23日回信說:「元月五日手示,昨始遞到。晚於上月二十日即得惡耗,又看到李慎之先生在《新民晚報》上的文章,以及新華社的報導。默丈走得如此灑脫,真似化鶴歸去,其境界遠遠超越塵世。我想若追隨眾賢之後,寫悼念文章,不如寫一本書作為永久的紀念」。我在信中還提道:「上月在南加州與何炳棣先生聚談了幾次(記得默丈在信中提到何先生與你有姻親),何先生看到我寫的《史傳通說》,笑稱『儼然錢體,難怪他會視你如忘年交』。我聽後慚愧之餘,又感榮幸」。
我寄給錢先生求教的拙撰之中,他的確最喜歡《史傳通說》一書,於1988年12月16日來函曰:「奉書及惠賜新著,喜甚。弟序之、題之,兄猶以為未足,並以拙稿傳真,榮寵至矣!何以克當?新著快讀一過,學識明通,詞筆雅適,新舊學者,儕輩中無足偶比;齒及不才,再三再四,獨不慮偏愛之譏乎?是則美中不足耳!」我更感激的是,錢先生於讚賞之餘,也指出書中的缺點:「大著已卒業,通識博聞,益我神智,開我心胸,必為名世之作。體例極具條貫統紀,吾國《史通》而後,無此綜賅之著,而文筆亦明暢可誦。百尺竿頭,求更進一步者,則援征近世學人著作較夥,求之古籍者較少。即就第一篇引拙著,『非記言乃代言』一節論之,弟原引Livy, Hegel既早在當世學人持此說之前,而Hegel之言,實即本於Thucydides自道(詳見《談藝錄》補訂本頁363-365)。兄先引Thucydides自言,而附近世學人之說於後,庶幾窮源探本,而非數典忘祖矣」。又說:「讀吾國及歐美近日學人著述,每有「To cite as an authority a modern academic where he may use a classic author」之歎,故於兄有厚望焉,不惜遭高明之嗤鄙也」。
曾有人批評錢先生「厚古薄今」,不重視近人著作,其實是誤會,他要強調的是「窮源探本」,重視原創。古典成為經典自有其高度的原創性,後人引用闡發,不能掠美。借用錢先生的話說:原創者是「說自己的話」,引用者是「說人家的話」,不能「用自己的嘴,說了人家的話,硬說嘴是自己的,所以話算不得人家。」做學術研究勢必要認清誰說的是自家的話,誰說的是別人的話。
2003年10月拜訪楊絳
我於2003年10月赴天津參加梁啟超學術研討會後,於16日轉往北京。翌日九時半往訪楊絳先生。進門見客廳如舊,牆上改掛陳石遺的對聯與條幅各一。楊先生說我的「槐聚五論」,文長百餘頁,很能闡釋鍾書的想法,惜鍾書不能見之。她氣色甚好,健步又健談,只是有點耳背。她說錢鍾書留下不少尾巴由她來收拾,有許多煩心的事。
她送我《圍城》中英文對照本,並簽名代奉,又示我已出的手稿影印本三巨冊,十分壯觀。楊先生特別提到,鍾書晚年很欣賞陳寅恪的詩,曾說早知陳先生如此會作詩,在清華讀書時,一定會選陳先生的課,成為恩師,但也不必諱言,他們在釋詩上有不同的看法。
楊先生說:夏志清寫文章談《我們仨》說錢瑗嫁給工人,一事無成,皆非事實。錢瑗先後二次結婚,夫婿都是書香門第;而她的英語教學事業在北師大有目共睹。楊先生說:夏捧錢鍾書卻又捧張愛玲,而張在淪陷區上海曾參與東亞共榮活動。夏志清稱楊絳為「大姐」,因他曾court小妹楊必。接著楊先生說:有一位海外作家,寫錢鍾書傳頗令她失望,她提供的資料未善加利用,卻多有侵權,最不可取的是引用明顯不實之事,雖略做辨正,卻又何必?
午時吳學昭女士來,我們步行至三和居午餐。楊先生很少外出吃飯,文革後這是第二次,上一次是與親家吃飯,吳女士說善儀與我的面子大。三和者,天和、地和、人和也,名菜有清蒸桂魚、香酥雞、紅燒烏參。錢先生生前有意將所藏《柳如是別傳》相贈,其中頗多批注,但吳女士在席間說,此本已不存在。楊先生於錢先生身後,整理編輯遺稿,不遺餘力,大量讀書筆記之出版,嘉惠學子,闕功至偉。楊先生十餘年來勤於練字,書法亦已自成家。錢先生生前所謂「最賢的妻,最才的女」,誰曰不然?楊先生於2016年5月25日才與世長辭,享壽105歲。
讀學孤行,置毀譽於度外
語云:「名滿天下,謗亦隨之」,錢先生亦難免。錢學得自天賦、得自家學、得自時代。而三者,後人難以兼有。錢先生與世無爭,有如市隱;然而凡具風骨的學人,多少有「知識人的傲氣」,何況錢氏博學多識,論文閱世每能推見至隱,不免直言無忌;固然有人賞識,然亦有人難以忍受,嘲諷其不饒人之性格,視其批評為罵人,最顛倒黑白者,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為熱衷名利。其晚年盛名非其預期,更非追逐可得,只因時空巨變,其學始大顯於世。但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寧,自歎「浮名害我」。
錢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,北美名校屢以講座邀請,西歐漢學會議以貴賓相招,均一一婉拒。利由名而來,無非是暢銷書的稿費,最後錢家所得之巨額版稅,由楊絳先生全數捐作清華獎學金,嘉惠學子,令人感佩。
錢先生獨學孤行,置毀譽於度外,自謂已至諛不喜而毀不怒的境界。但盛名之下,無端之傳聞不斷,仍使他感到困擾,於言談間感歎「老糊塗信口開河,小鑽風見縫插針,一人言虛,萬人言實」,殊覺無中生有、積非成是的無奈,嘗告誡我輩曰:見此等消息,必存戒心,無採入傳記也。錢先生晚境如此,自比湖上朝天之龜,動彈不得,深憾「人海無風亦起波」,痛恨為「眾蠅所啄也」。
猶憶1982年2月返美前辭別,來書云:「得書知返美期逼,未能把別,益增惆悵」,並自謂:「七十老叟誦少陵詩:『明日隔山嶽,世事兩茫茫』之語,此別益覺淒警矣」!情誼如此,令我感愧不已。至今回想,當時吾尚在壯年,歲月不居,而今已八十老翁矣!
(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)
